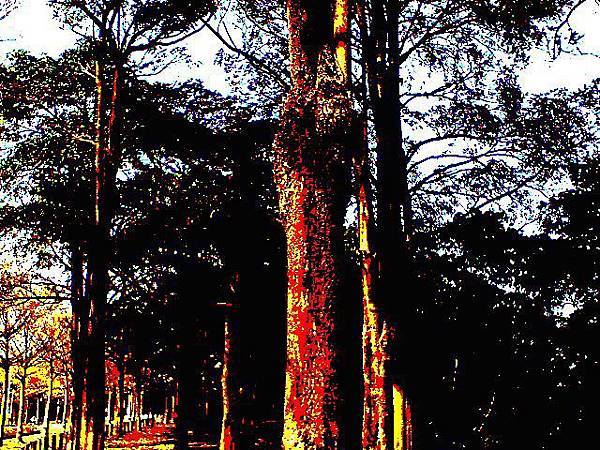
我過去以為生命可能是一種主觀的意識形態
一旦發現主觀價值然後必然勇敢跟隨
因此每個人似乎都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生命的出口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我們假想一隻身處於台北市101大樓的蟑螂,它正積極的尋找一個出口:不過,目的可能只是想如何活下去而已 。蟑螂是活在現在(雖然未來不一定活的下去),但至少可以使我們知道一件事:它在過去必然是活著。既然我們已經知道它在過去必然存有,是不是乾脆忘記會比較好?
『遺忘對於行為的重要性,就好像光線──乃至於黑暗──對有機生命的重要性。沒有記憶還有可能過活──甚至是很快樂的過活。然而,沒有遺忘而要過活,卻是不可能的 。』
尼采說過這麼一句話。
leben zu können是『能夠活下去』的意思,但是Nietzsche卻告訴我們『遺忘』才有辦法活下去。這個說法符合加zu的不定式所顯現的語境,具有一種對主體『行動要求』的言說。但是,zu können既然屬於一種要求,那麼語意上就脫離了「現實性」,而具有一種『可能的』推測狀態。換句話說,『能夠活下去』必然不是一個全稱命題。因此,我們還必須關注sterben zu können(能夠死「既然是死,當然就沒有死下去的問題」)這個可能性。
康德認為,一個人維續自己的生命,是出於自愛自保之心,所以還未達到「善」(Tugend)的境界;可是當一個遭受極度不幸的人,即使他採取自殺的行動,一般人都可以理解,他卻選擇盡力活下去,他是「出於義務」(aus Pflicht)維持生命,而非僅僅是「合乎義務的」(pflichtmäßig)而已。
康德告訴我們一個sterben zu können的可能狀態,但是他話鋒一轉,順勢連接了「能死」與「能活下去」的鍊條,顯現了「能夠活下去以外的客觀價值」。『生』與『死』這個存在主義議題,或許真的不是一個可以加以分析的命題,尤其當國家、社會、經濟等相對於個人的外觀察對象出現時,所謂的此在(Dasein)將成為一種難以體會的意識流。


 留言列表
留言列表


